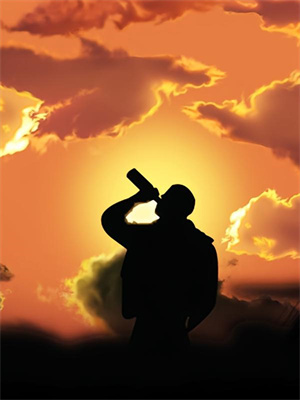简介
《契约解咒者》是“我和蘑菇总要死一个”的又一力作,本书以陆衍陆瑶为主角,展开了一段扣人心弦的悬疑脑洞故事。目前已更新146502字,喜欢这类小说的你千万不要错过!
契约解咒者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父亲书房的红木挂钟在午后的光尘里泛着冷光,钟摆悬在半空,像只被掐住喉咙的鸟。陆衍推开门时,黄铜指针正卡在两点五十九分,钟面蒙着的薄灰里,有七道新鲜的指痕,指尖朝向三点的位置 —— 与 1905 年透水事故的遇难时间记载莫名重合。
“每天这个时候都这样。” 福伯的拐杖在门槛上磕出闷响,他往钟摆下方的阴影里瞥了眼,那里堆着几本蒙尘的账簿,书脊上的 “1925” 字样被虫蛀得只剩个 “5”,“老爷失踪前,总在三点整锁门进书房,谁叫都不应。”
陆衍凑近挂钟,玻璃罩内侧凝着层白雾,擦净后露出齿轮的咬合处,缠着几缕黑色丝线。这发质与陆瑶发间的、伞骨上的如出一辙,扯断时丝线渗出的暗红汁液,滴在钟座的雕花里,竟凝成个极小的 “7” 字。左胸的青斑突然发烫,腕上矿工剪影的镐头同步落下,疼得他几乎弯下腰。
两点五十九分五十秒,钟摆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,不是左右摇摆,而是绕着轴心旋转,像在井下搅动铁链。齿轮摩擦的尖啸钻进左耳,与契约堂锁链拖地的声音同调,陆衍数着转动的圈数,不多不少正好三十七圈 —— 与 1905 年透水事故中丧生的矿工人数一致。
“咔嗒。”
三点整的瞬间,指针突然倒转,从三指向二指滑动,留下的轨迹在钟面烧出焦痕,形状像条煤矿巷道。陆衍盯着那轨迹,发现分支处有七个黑点,与陆瑶后颈青斑里的矿灯标记完全重合。更诡异的是,倒转的指针在玻璃罩上投下的阴影,竟在地面拼出残缺的契约书图案,第七页的位置空着,边缘泛着青灰色的光。
“这钟是光绪年间从德国运回来的,” 福伯的声音发飘,他往陆衍手里塞了块棉布,“擦不得钟面的焦痕,去年有个丫鬟想擦掉,第二天就僵直在煤矿井口,舌头被自己咬掉了,手里还攥着块钟摆碎片。”
棉布刚碰到焦痕,挂钟突然发出 “呜呜” 的低鸣,像矿井通风管破裂时的杂音。陆衍翻开父亲常看的《商业通论》,书页间的硫磺味浓得呛人,第 7 页的折角处,父亲用铅笔写的小字正在渗墨:“暗格在《资治通鉴》下册。” 墨迹晕开的边缘,浮出个模糊的人影,缺了左耳,帽檐压得很低,与照片里第七排左数第七个矿工的轮廓完美契合。
书页突然自行翻动,停在夹着书签的地方,上面印着煤矿开采的示意图,七号井的位置被红笔划了圈。陆衍用指尖点向红圈,纸面突然凹陷下去,露出底下藏着的半张照片 —— 父亲站在煤矿井口,左胸别着半块玉佩,接缝处的 “赵” 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身边站着个穿蓝布衫的女人,左脸有颗痣,与母亲火堆里烧剩的布带上的字迹如出一辙。
挂钟的倒转还在继续,指针扫过钟面的 “12” 时,书房的镜子突然蒙上层白雾。陆衍回头望去,镜中自己的后颈处,竟也长出块青斑,形状与陆瑶后颈的一模一样,巷道纹路里浮出无数个小人影,都穿着矿工服,正往深处钻去。
“您也有?” 福伯的拐杖 “哐当” 掉在地上,他后退着撞在书架上,《资治通鉴》下册从顶层滑落,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,“老奴早该想到的,陆家长子哪有没青斑的……” 他突然捂住嘴,像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,眼睛死死盯着镜中青斑的位置,瞳孔里映出个缺耳的矿工,正举着镐头往陆衍的后颈砸来。
陆衍冲到镜子前,镜面的白雾擦净又凝,反复三次后,镜中的青斑突然扩散,巷道纹路里的小人影停在第七个分支处,齐刷刷地转身,黑洞洞的眼睛对着他。倒转的指针此刻指向凌晨三点 —— 与父亲书房挂钟倒转的时间、煤矿井口递烟仪式的禁忌时辰完全一致。
“地脉在数人头呢。” 陆衍听见极细的低语,像是父亲的声音从挂钟里传来,“三百零七个,还差两个。” 他望向钟摆的阴影,账簿堆里露出个暗红色的角落,抽出来看,是本皮质日记本,封面的 “陆景明” 三个字被血浸透,翻开第一页,1925 年 10 月 15 日的日期下写着:“血月夜,见地脉真形,青斑非咒,是门。”
挂钟的低鸣突然变调,像无数个矿工在同时哼唱号子。陆衍按父亲的提示,抽出《资治通鉴》下册,书脊的第七个装订线处有个细小的凹槽,插入挂钟的钥匙后,书架 “咔嗒” 弹出暗格。一股浓烈的硫磺味扑面而来,与煤矿井下的气味丝毫不差,暗格里的桑皮纸契约书,前六页用朱砂写着 “每代献祭属龙族人”,第七页空缺,首页 “属龙者祭” 被红笔划圈,旁边有父亲的批注:“血月可改命,需赵脉。”
契约书的纸页薄如蝉翼,透光看,纤维里嵌着细小的血丝。翻到第三页,“1905 年补充条款” 记载:“透水事故后,祭品需带青斑,斑显巷道纹者为上选。” 陆衍摸向自己左胸的青斑,突然发烫,与后颈的青斑产生共鸣,像有两股热流在血脉里交汇。
挂钟的指针倒转到凌晨三点时,突然停住,齿轮的咬合处渗出粘稠的液体,在钟座上积成小水洼。陆衍凑近看,水洼里映出的不是书房的景象,是片漆黑的矿井,父亲正举着矿灯往深处走,矿灯的光晕里,无数个缺耳的矿工对着他鞠躬,左胸的青斑在黑暗里闪闪发亮。
“老爷说,这钟能显过去事。” 福伯的声音带着哭腔,他指向水洼里的矿井,“1905 年透水那天,钟摆也这样停过,水洼里映出三百多个矿工在井底排成队,就等着上岸呢。” 他的拐杖尖在地上划出圈,圈住那些液体汇成的细流,“您看这水,往暗格的方向流了七次,跟当年矿工的逃生路线一模一样。”
陆衍将日记本塞进怀里,皮质封面的血渍蹭在衬衫上,与左胸的青斑烫在一起。他突然想起妹妹呓语里的铁轨尽头,龙形门环此刻在脑子里变得清晰,与挂钟齿轮的咬合处完美契合。倒转的指针留下的焦痕里,渗出的液体在地面拼出 “赵” 字,与母亲火堆里烧剩的布带上的字迹如出一辙。
挂钟的玻璃罩突然炸裂,碎片溅在《商业通论》上,第 7 页的折角处,父亲的字迹突然变得清晰,像是刚写上去的:“双玉合璧,血月照星图。” 墨迹晕开的边缘,浮出半块玉佩的图案,与自己怀里的正好互补,接缝处的 “陆赵” 二字在阳光下泛着红光。
书房的挂钟彻底安静下来,只有齿轮的咬合处还在渗出液体,在地面积成个小小的水洼。陆衍望向窗外,石榴树的七个青果在风里轻轻晃动,果皮上的人脸轮廓对着书房,眼睛的位置渗出的汁液,在地上积成个 “7” 字。他知道,父亲书房的钟不是普通的计时器,是地脉的脉搏,是 1875 年契约的计时器,是三百零七条人命的呐喊。
福伯已经吓得说不出话,只是指着暗格的方向摇头。陆衍握紧那本皮质日记本,封面的血渍与左胸的青斑贴在一起,烫得像两块烧红的烙铁。他知道,发现暗格不是结束,是另一个开始。那些藏在挂钟里的秘密,那些父亲留下的线索,那些陆赵两家的血脉纠葛,都在等着他去一一解开。
三点十五分,挂钟的指针突然恢复正常转动,留下的焦痕里,渗出的液体在地面拼出完整的契约书图案,第七页的位置,慢慢浮现出 “和” 字的轮廓。陆衍望向镜中的自己,后颈的青斑已经消退,只留下七个极小的血点,像被矿工镐尖扎过似的。左胸的青斑还在发烫,他知道,这只是暂时的平静,当血月再次升起,当双玉合璧,当第七页的秘密被揭开,等待他的将是无法逃避的宿命。
书房的门在身后 “吱呀” 一声关上了,门轴转动的声音里,陆衍仿佛听见无数个声音在低语,像 1905 年的矿工们在井底哼着号子,像挂钟倒转时的齿轮声,像父亲日记本里的叹息,最终都汇成两个字:解契。
解契的关键,到底藏在《资治通鉴》下册的暗格里,还是挂钟的齿轮中,或是那半块尚未找到的玉佩上?陆衍望向窗外的石榴树,七个青果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,果皮上的人脸轮廓里,眼睛的位置渗出的汁液,在地上积成个小小的水洼,映出无数顶矿工帽在井底沉浮。
他知道,父亲书房的钟只是个开始。当挂钟再次在三点整倒转,当第七页的秘密被揭开,当双玉合璧显露出 “陆赵同源” 的真相,西跨院那扇钉着七枚黄铜钉的木门后,藏着的将是陆赵两家百年诅咒的解药,是三百零七条人命的安息之地,是 1928 年血月之夜必须完成的救赎。
书房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,挂钟的齿轮咬合处还在渗出液体,在地面积成的水洼里,父亲举着矿灯的身影越来越清晰,左胸的青斑在黑暗里闪闪发亮,像是在指引方向。陆衍握紧怀里的日记本,皮质封面的血渍与左胸的青斑产生共鸣,烫得他几乎要听见血液里流淌的号子声 —— 那是 1905 年的矿工们,在黑暗的井底,用最后一口气哼出的调子。